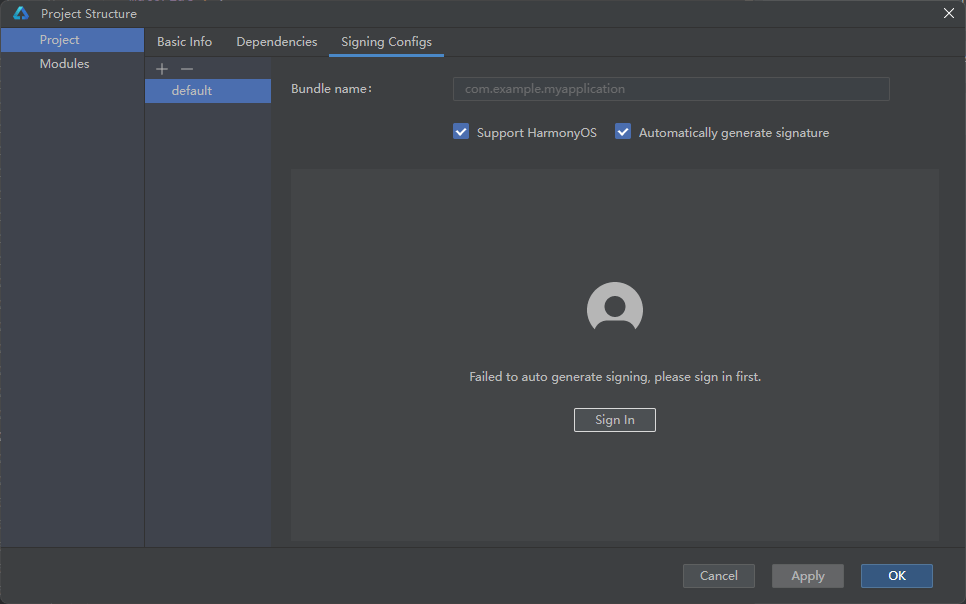*CYZONE特写,大时代惘闻录
几十万人,有几十万张脸、几十万种个体意志,即便放在中国娱乐业时间轴里做纵向对比,这也是一支庞大、复杂的组织,甚至称得上是一个现代社会学里的标志性事物。
虹桥T2 VIP通道出口,吴亦凡出现了。黑色保姆车就停在路边,他本可以径直走过去,直接乘车离开。
不过他没有,而是侧身走向了林光宇所在的人群。她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可能吴亦凡就这么走了,她原本想。「其实在国外接机更容易点,他有时会走普通出口,更可能跟粉丝说上话」,林光宇说,「国内就不好说了,也有等几个小时接不到人的情况。」
她们一起等在通道的另一面,在围栏外喊吴亦凡的名字,吴亦凡走来打招呼,她们又为他唱生日快乐歌,他完整听完,向人群缓慢地鞠了一躬,表达谢意,才一边挥手跟大家告别一边离开。
就接机来说,这次算很有收获,这收获让林光宇觉得感动,她想,吴亦凡完全可以直接上车走人的,可他没有,而这种小事正体现了偶像的教养,「也觉得他是特别温柔的人。」
和林光宇一样,和所有其他偶像的粉丝一样,她们乐于从吴亦凡的行为细节里,观察其优秀的特质,并藉此进一步确认、强化自己的崇拜与追求。
吴亦凡有多少粉丝?按江湖传言,这位偶像艺人身后历来有个「粉丝三千万」的说法;按社交网络数据,本季《中国新说唱》收官当天,他的微博粉丝突破四千万;按照粉丝内部观察,其中保持日常关注并频繁参与团体协作的忠粉,在数十万量级。
几十万人,有几十万张脸、几十万种个体意志,即便放在中国娱乐业时间轴里做纵向对比,这也是一支相当庞大、复杂的组织,甚至称得上是一个现代社会学里的标志性事物。
她们通过社交平台构建了组织结构,它好像一座精密的巨型钟表,无数个光泽各异的金属齿轮交错排列,咬合,转动,它承担着巨大的信息吞吐量,循环流转、调度着每个节点,并最终向外输出最为恰当的集体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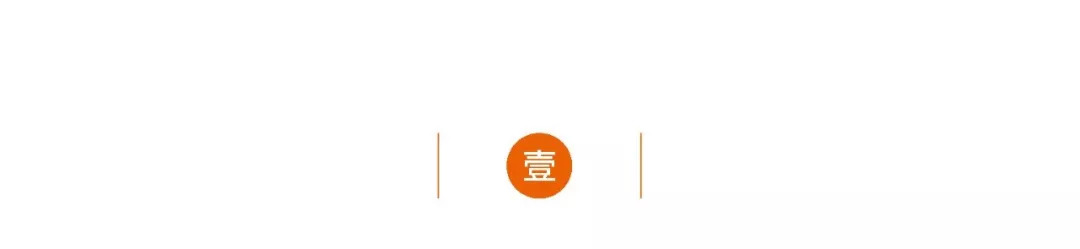
「拒绝一切碰瓷」
先从7月末与虎扑的故事说起。
那天下午,虎扑社区微博管理员给此次与吴亦凡粉丝的争论下了定义,一个口号式的定义,叫「战争」,「这是一场战争,JRS(虎扑网友)准备好了吗?」
此前一天,吴亦凡「反黑组」在微博发布关于虎扑网帖的举报链接,发酵一整天后,步行街论坛被点燃,社区陷入狂欢,当天有数百条网帖跟进讨论,其中不乏「大字报」式的檄文,甚至连点亮功能都被修改为「skr」——这也可以视其为修筑战前防御工事。
其间,曾经有数个帖子提出过对虎扑官方态度的质疑,有人不理解,为何论坛官方出面助推冲突,但这些讨论并未引起波澜,很快就淹没在针对吴亦凡和梅格妮(吴亦凡粉丝,同「每个你」)们的声讨浪潮里了。
当时,多数JRS认为,「战争」一触即发,他们要思量的核心在于己方网友人数、战力如何,以及虎扑官方的答题等防御机制是否有效。
只是现实蹊跷得很,吴亦凡粉丝反应激烈,却没有在虎扑现身。
田沁从练习生时期开始追吴亦凡,三年前,还在读高中的她去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偶像生日会,同场的是一群同年龄层的年轻女孩。
在耀眼的气氛里,田沁觉得感动胀满胸臆,她也意外地意识到,这些同龄人在网络前后呈现出巨大的分裂感。
2018超级企鹅联盟明星赛红蓝大战,球迷中有人举起画幅声援吴亦凡(图源东方IC)
旁边几位女孩举着沉甸甸的「凡」字灯牌,莹黄色的光映着暗面一排冻得通红的笑脸,原来她们生活里是温顺的,而一旦遇到吴亦凡在网络上遭遇「攻击」,她们中有些人便会立刻披上微博小号外衣,化身「准备恶斗的小公鸡」,咄咄逼人问候对面。
按这个逻辑,与虎扑的冲突,自然应当是一个令她们无法容忍的事件。
可她们没有出现,这显然是悖论,背后是整个「虎扑&吴亦凡」事件中最值得玩味的逻辑之一:粉丝们用集体意志的贯彻消解了个体情绪。
所有人枕戈待旦之时,吴亦凡粉丝的怒火与虎扑论坛完全错配,很少有梅格妮在虎扑发帖。
一位吴亦凡粉丝对《创业邦》说,当晚她所在的所有QQ群里都在号召粉丝们「不要直接在虎扑评论,控评去微博举报」。
这些行为背后的理由之一是微博作为更加开放的社交平台,天然是粉丝们的主战场;理由之二,是拒绝给虎扑提供新增注册用户与点击量。
「不论是虎扑,还是其他流量明星,我们拒绝一切碰瓷」,在前线追了多年的站姐钟谨说,因为吴亦凡早已是「流量Top」,那么在所有与其有关的博弈中,首先要杜绝被有心人蹭热度与流量。
在这些事情上,她们习惯于对每一次冲突里的每一个参与方的行为做深度思考,这也直接决定了双方后续的敌友关系界定:比如此前一档说唱节目导师由某位歌手更换为吴亦凡,导致双方粉丝「正常骂战」,其间,对方工作室向吴亦凡的某几位大粉发出了律师函,「大家就一脸懵,还有这种新式碰瓷手法吗?」
在整个事件里,另一个焦点角色虎扑始终对此事讳莫如深,并谢绝了采访邀约。
「没法儿摘滤镜」
和所有接受采访的女孩一样,谈话伊始,吴亦凡的大粉钟谨就表了个态,说她「没法儿摘滤镜」,也就是说,她不可能以任何不倾向于吴亦凡权益的立场来谈论问题。
对粉丝来说,这种滤镜同时又像一卷皮尺,用来衡量尺度,寻找分寸。
要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娱乐圈的每一番争斗背后,都有多方利益、人情纠葛,作为粉丝中的KOL,钟谨觉得,复盘推演是自己的职责,她要清晰、准确地维护偶像的权益,首先必须厘清台面幕后各方的利益关系。
吴晓益追了吴亦凡多年,现在从事艺人经济工作。这也算得从粉丝层面向艺人经纪行业输出方法论的经典案例,在她看来,虎扑事件中人为操作的理由十分充分:综艺节目制作方与平台为求热度,营造或借势冲突是常见的事,此外,很多宣传团队也会引导负面事件转向正面。
私下推论不是公断,对她们来说,结论无须苛求严谨,只求清晰,所以结果倒推的办法就很好使。如果把虎扑事件视为一次营销,那得说是玩得成功又高级,卷入其中的虎扑、吴亦凡、爱奇艺、参赛歌手甚至是贩卖虎扑账号的商家,均是流量和热度的受益方,但钟谨坚持认为事有蹊跷,「如果虎扑真心不希望节目有流量的话,为什么要助推「skr」这个热词?」
另一位受访的粉丝则认为,由吴亦凡微博称「不知动了谁的奶酪」来看,事件背后可能是由娱乐业同行竞争驱动。
在条分缕析的过程里,滤镜的存在意义就是,提供方向感。
尽管吴亦凡当期发的歌同样获取了很高的播放量,但在钟谨们看来,她们的偶像仍然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受害方,因为损失了口碑。同时,很多梅格妮也对吴亦凡工作室不甚满意,「他们发了个声明就消失了。」
而吴亦凡的表现,则被认为非常得体。甚至其微博发声,并发表Diss Track,在吴晓益眼中也是某种义举,「他觉得一帮维护者我的姑娘,因为我受了委屈,我看不下去,所以就站了出来。」
只是,工作室官方态度中的晦暗不明之处,以及客观上获取的歌曲流量红利,是否也意味着,其中也有多方达成默契的可能性?钟谨则明确拒绝将此纳入考量,「我们粉丝其实只能知道工作室希望我们知道的事情,也只做到粉丝能做的。」
吴亦凡的微博粉丝数量已经超过4000万,按照钟谨的观察,其中日常持续打卡、活跃度较高的「唯饭(只追某一明星的忠粉)」约在数十万量级。
她们懂公关、运营、流量与组织管理,也有充足的购买力,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以年轻女性为绝对主导的庞大社群,在很多个面向上展现出了强大的自觉性,与虎扑的这一场冲突中,她们展现的应对策略与思考方式,正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进入游戏」
和吴亦凡星途上历经的杂驳曲折不同,其粉丝群体从练习生时期发端,整个组织结构的成长是线性的、流动的。如今,通过贴吧、微博、QQ、豆瓣等社交平台及工具,有数十万人将她们的日常交汇起来。
她们绝大多数是女性,介入互相的生活不算多。有人家境优渥各处跟飞,有人穷到凑不出机票钱,有人为偶像学了各项技能,有人追星追到学业荒废,有人在微博卷着乡骂做泼妇、口无遮拦,有人在校园裙角飞扬谈恋爱、甜美可人,有人出入映着晴空的高级写字楼,工作体面,有人双眼前挂着厚厚瓶底,点着下巴背单词……几十万人,有几十万张脸、几十万种个体意志,即便放在中国娱乐业时间轴里做纵向对比,这也是个空前庞大、复杂的组织,甚至称得上是一个现代社会学里的标志性事物。
她们并未遵循任何组织管理理念或者指导,每个枝节都是自由生长而来。作为艺人,在练习生时期需要面临大量的平行竞争,而经纪公司几乎不会做任何资源配置与倾斜。
以吴亦凡、鹿晗等人为例,尚未出道时,便有粉丝在宣发等事务性工作上投入资金、精力与支持,到2014年吴亦凡归国,他的粉丝们由其个人业务需求出发,开始自发地把个体的、抽象的热情整合起来,再行分发,以构建更加有效的组织结构。
按照钟谨的理解,吴亦凡的粉丝之前与虎扑用户「河水不犯井水」,如果非要说有交集,也顶多是吴本人好打篮球,打过几场All-Star名人赛,引起过虎扑关注。
此次微博名为「银河鲨鱼护卫队」的站姐将虎扑步行街上与吴亦凡相关的负面贴子地址、举报原因与举报方法详细整理后被虎扑发现,引起擦枪走火,该微博上述行为属于吴亦凡粉丝的「反黑组」日常,此事也可以理解为,外界偶然窥见这台机器的运作时,由双方认知差异,所引发的摩擦。
在成体系的粉丝组织结构中,反黑组隶属于后台职能部门,与其平行的还有资源组、数据组、翻译组等,每天整理与偶像相关的负面信息,集中发布在某些平台,并把「控评」工作分发下去,也是反黑组最主要的常规工作。而少数工作、课业不那么繁重,经济条件较好的粉丝则更多会「跑前线」,在机场、工作地拿到大量第一手的照片、资讯,并经营微博等站点,被称为「站姐」。
(按类型、职能与属性等不同维度划分粉丝群体)
但是对经营公共人物品牌来说,反黑只能守住下限,真正引导其在更高层级的商业价值上博弈的,还是流量数据。
数据背后有代价,无论你是否认同,如果要进入这场关乎流量的商业游戏,必须要遵守规则,要去「运做」,而这也是所谓「数据组」的存在意义。
「废物」,谈到流量数据,吴晓益干脆地甩出来这两个字,在她看来,数值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娱乐圈尤其是时尚圈内,市场对艺人相关数据很是看重,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偶像的带货能力。
为了给偶像撕资源,粉丝常常大动干戈地做/买数据。这包括但不限于转评偶像的微博,成果会呈现在微博榜单;若偶像出歌则打歌,整理音源数据,包括排名,主打,MV播放量等数据;帮偶像打榜投票,包括明星势力榜、百度百科明星人气榜、百度搜索风云榜、寻艺新媒体艺人指数榜、微热点热度榜、超级话题、百度贴吧等诸多榜单。
随着游戏进程深入,规则也变得越来越难。
例如,在运作微博转发量时,只有不太受到关注的小艺人才可能购买微博大号的转发做数据,反而越是当红的艺人,越需要精细化运营。目前每个微博小号往往转发40次左右就会被封号,因此「水军」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而艺人社交平台最终数据的高低,仍然取决于其粉丝团的人数、忠诚度、管理水准、运营效率等硬实力。
在应援的执行上,则有更加细化、明确的策略出台来应对每一件事务。10月19日,吴亦凡的新专辑开启预售,但微博上多个站子都在呼吁粉丝「不要参与Pre-order」。
理由在于艺人「国际路线」的定位。对吴亦凡来说,要发新歌,最重要的成绩单是iTunes美国总榜和Billboard榜单,那么就必须吃透榜单规则,按规则出牌。微博上,名为「FanGalaxy_凡骑吧」的站子发帖解释,「正式发行的日期是11.2,我们冲首日及首周的成绩最重要。一个号只能买一次。你确定你的号一定在11.2或11.2之后一周内买到即可。」
尽管品牌方对其中某些数据的水分含量心知肚明,但他们也认可大部分数据、榜单成绩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而有些数据也仿佛失去了坐标轴的曲线,它们的相互攀比、竞争,本质上也是一种相互依存,只有借助彼此为坐标,方才使得自身有存在价值。
粉丝生意经
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钟谨总是处于短途的「在路上」。她会很早到公司,到前台「嘟」地打卡,再掉头去机场,奔赴吴亦凡开工的城市,为偶像站台2小时,现场抓取照片、资讯,当日再折返回居住城市,回单位打卡。以至于,三个月间便刷完了一张存着十万元的银行卡。
有些站姐更是会跟着吴亦凡「满世界飞」,她们是粉丝中距离偶像最近的人,不仅与工作人员沟通密切,甚至和偶像本人也有着一定的交往。在整台机器中,由于承担着一线的内容分发职能,站姐们事实上成为一个个内部流量流转的节点。但与社交网络上多数的流量节点相比,吴亦凡粉丝站子的商业变现又十分有限。
钟谨很早便开设了站子,但她并不愿透露自己所管理的账号名称,也不止她,不公开表明身份,是经营站子的一个暗线规则。一方面,这是粉丝,尤其是粉丝KOL对自己真实生活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免去某些麻烦。
麻烦的可能性,就潜藏在商业模式里,因为某种意义上,这是粉丝利用偶像的资源反向变现。
2017超级企鹅篮球名人赛红毯仪式,粉丝在场外翘首以待吴亦凡
除了贴吧之外,微博站子可以说是粉丝流量最集中的区域。在网络上,流量天然是个变现工具,很多站姐会将手里资源藉此变现,其中,PB(即photobook,粉丝制作的图片写真书)是最常见的一种产品形式。
一位豆瓣网友曾解读过PB的生意经,首先其成本低廉,一本mini PB,B5大小,30P,500本起印,成本5元/本,1000本起印的话,则为3元/本,2000本起印,更可以达到2.5元/本。但站姐出售PB,最少也要数百元起。
据该网友称,PB本身就处于灰色地带,一般都是在粉圈内低调出售。其灰色部分在于多个层面,例如私拍的明星照片多数未获商用授权,助长跟踪、偷拍风气,不时有圈钱跑路的现象出现,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PB本身就是典型的非法出版物。
但由于又承担着信息交互、维持粉丝群体热度、以及补贴站姐营运成本等职能,PB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在暗线规则内,PB始终是被默许的产品,但站姐卖PB赚来的钱,除了补贴成本,余款理应返还为偶像做应援,虽然是个体经营赚来的钱,但「私吞」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而「爬墙(同时追求其他明星艺人)」则更是「重罪」。
这其实也是所有经手资金流转的粉丝面对的课题,要应付整个组织机构内无处不在的隐性监督。
资金流转这件事,在一些近年出道的艺人粉丝组织里更加敏感,因为纯粹的「集资」行为频率更高,如果出现大的问题,比如账目对不上,应援出错影响艺人形象,这些都会被粉丝「挂」,管理和组织者可能被要求道歉,甚至交出权力,退出组织。
例如,此前邓伦全球后援会在应援活动里就出了岔子,送至现场的烧饼、水果等物资,被讽刺称「又贪又蠢,捞钱捞的傻子都知道有问题」。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涉事分会会长、副会长引咎辞职,后援会管理组就地解散并公开招募,承诺公开透明。
有限变现的流量
吴亦凡的粉丝站子里,养不来流量商人。
几十万人的关注,为吴亦凡粉丝群交织出一个牢不可破的监督机制,在更大范围内杜绝贪腐,同时也隔绝了商业化个人或机构的介入。质言之,怀着纯粹的商业考量,去从事吴亦凡粉丝流量生意的行为,在组织内是不被接受的。
即便社交平台被认为供给的是原生流量,用户的交互仍然需要以内容驱动,因此常年追随在前线的站姐——在梅格妮中大约只有数十人——是链条中的内容分发肇始点,她们手中的站子,也是流量最为集中的节点。
换句话说,如果经营粉丝的流量生意,开设站子是最适合的路径,问题在于,这门生意很容易就会被从内容入口处掐灭。虽然市场上日常也可以买到一些图片和消息,但如果不是跑在一线的站姐,很难稳定地获取街拍图片和资讯等内容。

2018年8月,吴亦凡拿奖归来一脸疲惫,粉丝拉横幅欢呼欢迎
(图源东方IC)
「我们作为前线感觉得出来,一个新人进来,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底细。」
「你只是买图,从来没有在现场出现过,我们觉得你不肯为吴亦凡花钱,还想赚钱的话,首先就把你『搞死』。」钟谨说,「如果一个站子去不了几次现场,PB却卖的很勤,大家心里都有数的。」
吴晓益觉得,这一方面说明了吴亦凡的粉丝更加热情纯粹,另外也是时机使然,「以前大家对这事认知不清晰,没人想到卖货能跟应援一起做,而现在圈子已经很稳固了。」
最近几年蹿升迅猛的新晋艺人粉丝群里,商业化做得更加通透,由于组织群体仍然在不断扩张中,持续出现增量人群,人群意味着红利,因此有大量空间可以执行商业行为。
以PB为例,吴亦凡的PB,卖到大几百册是个不错的表现,对站姐来说,这个数字能做到盈亏平衡,或小有盈余;而蔡徐坤的PB则全然不同,动辄可卖出几万册,这种小爆款背后,通常意味着数十万元的利润。前不久,蔡徐坤的生日会门票被炒至天价,让钟谨直呼没见过这阵仗,有人捧着三万五满世界找门票,就为了见蔡徐坤1小时,「疯了吗这是」。
由于正在从事艺人经纪工作,吴晓益此前对照自己带的艺人,做了个蔡徐坤的数据统计。她发现,在《偶像练习生》上线之后的半年内,蔡徐坤的各项粉丝数据表现堪称「现象级」,比赛期间4个月粉丝上涨455万,而比赛结束后又持续蹿升起了100多万。「太可怕了,难以想象这是个刚出道新人的数据。」
此外,在新浪微博的超话中,蔡徐坤的表现也很突出,以2018年10月23日为例,截至上午9时,蔡徐坤在超话位列第1,签到超过19万人次,吴亦凡排名24,签到约4万人次。
从下半年承接热度的《创造101》、《SNH48第五届总选》活动来看,艺人应援更加令人咂舌,尽管曾出现了粉头卷钱等负面信息,但可集资数据一度分别达到了4000万元和7000万元。
不过钟谨认为,吴亦凡的横向对比,已经不在社交网络这个维度上,「他已经不太需要这种数据了」。
她认为,吴亦凡的商业价值已经脱离了应援层面,而是集中体现在商业代言上,即她们经常谈论的「带货能力」。吴亦凡的粉丝的目标是「带货王」,执行上也很简单,「送礼当送Burberry、首饰珠宝选BVLGARI,饮料就喝茶π」。2016年10月份,Burberry签下吴亦凡做代言,次年一季度,亚太地区零售额实现14%的逆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吴亦凡「带货能力」的体现。
当《创业邦》问到另一个吴亦凡粉丝关于对比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更干脆,「就是艺人和偶像的区别。」
统一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做出这样的假设,你也许感到不可思议——你生活在一个拥有数千家住户、十余万人口的高端社区里,家委会年初动员所有家庭集资建起一座街心公园;三伏天,获取居民集体签字同意放弃宠物饲养;年末则集体腾退,辟出这块地皮,建设高尔夫球场……
其实不单在于社区,对于稍微成规模的人群来说,这种集体意志的高度统一都是不可实现,乃至令人倍感荒诞的。
但在网络上,粉丝间,数十万人、数百万人却可以循着某种特殊的情绪去一起实现它,如果我们仍然将粉丝组织物化为一台机器去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高效运转背后最本质的基础,在于价值判断的统一。
对与吴亦凡有关的任何事物,在梅格妮的群体间,可以快速消化,实现价值判断,并以集体的形式输出反馈。
2015年11月,工体生日会,粉丝专注看向台上的吴亦凡
有些常用的判断会形成规则,比如说,前线的站姐跟着吴亦凡到处跑,在各地录节目时为其站台,是可以被鼓励的行为,但追私(跟踪明星的私人行程)则决不可接受——虽然明星本人的航班信息8块钱就可以在微博上买到。
也有道德层面的约束规则,比如同时追求两位明星艺人,是令人特别不齿的事情。
更多的集体判断,则被高效地应用在具体事件中,例如,前述与虎扑的冲突,以及与某位女艺人的合作,由于存在很大的「被碰瓷」嫌疑,就是必须回避的。对此相对,吴亦凡与刘亦菲的合作又被视为加分项,因为「好看的人就应该跟好看的人在一起」。
这些集体意志潜藏着驱动力,它会受到偶像本人的引导,但也有很多时刻,可以形成反向制约,最常见的标的是指向经纪公司与工作室的。
去年吴亦凡工作室不顾粉丝反对,接下了与某女艺人组CP的综艺节目,这令钟谨感到丧气,在那之前,包括她在内的很多站姐都在「疯狂地给工作室打预防针」,「就说对方惯用的宣传伎俩就是捆绑男艺人,但是工作室没有太当回事,后来果然被猜中了,再去控制就已经来不及了。」
粉丝圈里常年流传着类似故事:A工作室公开发信为工作失当道歉;B团队发错通稿;C艺人在直播中遭强吻,工作室两天后才做出反馈;D艺人微博管理员发错赈灾文案等等。甚至有媒体人发文反问,「世界上有『让粉丝满意的艺人工作室』这种生物吗?」
粉丝往往会与工作室陷入一个长久的博弈、合作又制衡着的关系当中去,而粉丝在其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市场的买方亦或合约中的甲方,虽然内含一些自律条款,但更多时候,还是会将压力和焦点集中在艺人工作室上,用粉丝的热情去衡量对方的工作,并希望得到匹配自己付出的表现。
「你不可能指望经纪团队做好所有事,我们都会怀着一腔热情帮忙,公关需要成本,但粉丝是没有成本的。」一位站姐告诉《创业邦》。
「我们的判断标准是统一的,就是对吴亦凡好」,她说,「没有看上去还行,看上去还行已经算不好了,就必须得完美。」
「大家不明白」
无论是林光宇、吴晓益还是钟谨,她们对吴亦凡的情感表达,大多局限在微博、贴吧这类开放平台上。现实生活中,职场里,甚至在封闭的社交网络——例如微信朋友圈——当中,她们都不太会展露这一面。
她们清楚地知道,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粉丝是一个天然的偏见载体。
「粉丝可能在大部分人眼里算是异类,因为大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事情,为什么要一直追着那个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林光宇说。
极端个案也一直存在。今年13岁的陈画,为了追吴亦凡的行程,不声不响刷掉了妈妈2万元的信用卡——在家庭贷款尚未还完,信用卡为应急之用的情况下——这也造成了家庭关系紧张。有些粉丝好友不时会为其转账应急。她之前已经瞒着家里去看过吴亦凡参加的跨年演唱会,而如果信用卡的事没有暴露,此时她应该又在另一个现场。
其实粉丝、偏见甚至极端案例都不是新鲜事物。上世纪60年代,英美等西方社会人群对披头士团队的狂热,体现为成千上万的女性粉丝的狂热包围,最终留下了一个看上去诡异多变、难以描摹的词汇「Beatlemania(披头士狂热)」,一篇名为《 Beatlemania:Girls Just Want Have Fun 》的文章写道,1964年,穿着百慕大式短裤、预科生的高领宽松上衣,梳着蓬松发式的年轻女孩们,一边冲向警戒线,一边呼喊着「我爱林戈(Ringo Starr)」。
在上世纪60年代,这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文化现象」。美国塔尔萨大学传播系教授朱莉·詹森曾分析过粉丝被「污名化」和遭到社会歧视的原因,她认为,极端粉丝行为隐含着公众对现代生活的一种批判,粉丝身份本质上是对这种孤立的、原子化的现代生活的一种心理补偿。
半个世纪过去后,现代生活的意义变得更加未知。与当初的Beatlemania相比,粉丝文化这种社会现象,在市场化的作用下,套上粉丝经济的皮囊,也似乎变得更加稳定、可控。对于粉丝个体来说,也在集体意志下,更多地脱离那些极端的表现形式。
粉丝们追求这种平衡感,但并不期待理解,林光宇说,她从未期待让家人朋友明白自己为什么追星,「你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但平衡的存在是很微妙的。在澎湃新闻的一次采访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当等待的女孩们在昏暗中看到吴亦凡的剪影时,「一排排脸整齐地贴在玻璃上」,然后是吴亦凡的沉默,「多可怜啊,她们」,他暂停了采访,向窗外轻轻地摇了摇手机,随即尖叫声和闪光灯一齐疯狂闪现。
钟谨记得,就是这句话,造成了一批人「脱粉」。她为吴亦凡辩白,「他本意不是这样,本意是心疼大家在等他,可是那句话发出来,就有种『我看不起你们』的意思,话术这东西……」
吴晓益补充,「他本人对于中文理解不是很好,稿件审核一般是给到团队,但可能团队也没能意识到这句话里的不妥之处,而且如果挑的太细,还可能被对方觉得耍大牌吧。」
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关系,从来刀尖舔糖,坚固更脆弱。她们为偶像付出,追随他爱护他,在他出现负面消息时坚定地站在他身后,却在某些时刻,抵挡不住一句话里行间的误解。
粉丝文化仍然在迅速演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在某些时刻,偶像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高速的迭代会令某些局部的现实失衡,以至于呈现得愈加魔幻。
最近听来的一个故事,让林光宇头绪繁多,又觉得颇有意味:几位追前线的粉丝,在一架航班上偶遇,面面相觑,竟有些尴尬,因为她们意外地发现,与此前一起追的某次行程相比,粉丝仍是那几位,保镖仍是那几位,只是前面头等舱的那位偶像,换人了。
而钟谨最近则奇妙地发现前线出现了许多新面孔,其中不乏穿校服的小姑娘。前段时间,在《中国新说唱》现场,她能认出的也只有两个相熟的面庞,其他人都看着陌生。
新粉进来多是由于电影、新歌与节目的吸引,去年的《中国有嘻哈》可谓是功不可没。
截至2018年10月23日上午9时,吴亦凡最新的微博粉丝数为4277万。他的后援组织疆界依然在持续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