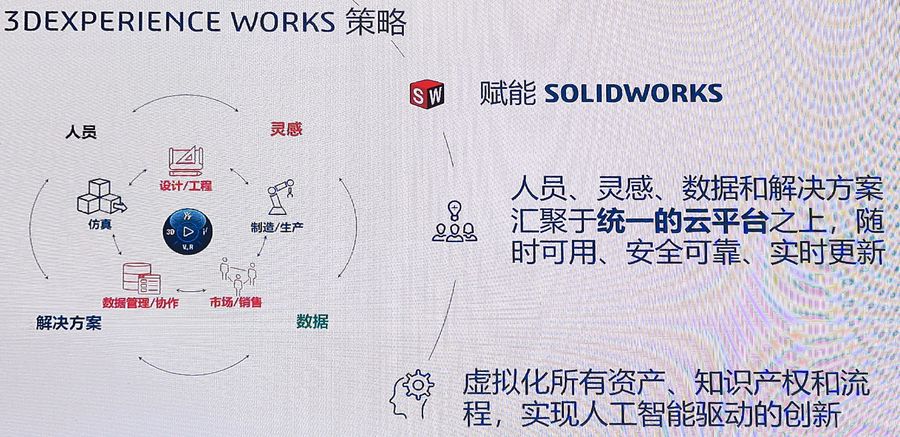马克已经迫不及待了。这种揪心的渴望让他辗转难眠。为了这一刻,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与这种渴望相关的各种产品。作为一枚货真价实的“果粉”,最近一段时间马克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了一件事上——苹果公司在悉尼的新店开张。
把马克形容成一位“狂热分子”一点都不夸张。他急切地准备着从加州坐15个小时的飞机去悉尼。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他站在悉尼街头这条超过4000人的巨型队伍里,他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他一起排队的人中,有很多都和他一样,在前一晚露宿在店前的广场上。马克告诉我,苹果在日本东京再开新店时,他还会第一时间赶到。对他而言,赶赴悉尼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意义——这是苹果在全球开的第40家专卖店。当我问他对这次行动的期待是什么?他回答道:拿到一件纪念T恤。
巧合的是——甚至可以说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苹果悉尼新店开业之后一周就赶上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来此访问。假如你刚刚从外星球来到地球,在看到满街的“果粉”和同时出现的成千上万天主教徒时,你可能会误认为“苹果”是这个星球上另一种拥有信徒无数的重要宗教——与天主教徒们一样,“果粉”们也认定对苹果产品的忠诚与信仰苍天可表。
那么,我的问题是:品牌与宗教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马克心中的那股狂热和10万多名天主教徒集结悉尼时的心理是否相同?
多年以来,我始终在与各种品牌的拥趸交流,他们中有哈雷·戴维森重型机车的“粉丝”,有Hello Kitty的狂热分子(其中一位竟然拥有超过12000件带有Hello Kitty图案的商品),也有醉心于爱尔兰健力士啤酒的拥趸,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品牌在其拥护者心中宗教般的地位所震撼。我最为好奇的是,这些品牌究竟是如何建立起如此强大的诱惑乃至归属感?
2004年,我开始为此进行一项为期4年的调查。这一次我不再采通过问卷和访问收集信息进行调研,而是决定借助之前极少被用于大规模调查的神经科学和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大脑扫描技术,以帮助我弄清楚品牌与宗教传播之间效果的异同。为此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了数千名基督教信徒志愿者,我希望实验结果能帮我验证一个问题:当苹果、哈雷·戴维森、健力士等品牌的拥护者在接收到所钟爱品牌的信息时,其大脑反应与虔诚的教徒接收到宗教符号刺激时的反应呈现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和大多数定量或者定性研究所不同的是,神经科学的调研很难在短期内完成。从开始规划实验目标、步骤到完成大脑神经扫描,得出实验结论,通常需要长达半年时间。为了解关于品牌营销和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真相,我们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且最昂贵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
当上千名基督教徒来到英国牛津附近的神经科学实验室时,他们兴奋异常。“这些机器真能显示我在想什么吗?”“它们能看出来我的宗教信仰?”“经过测试之后我的信仰会不会消失?”3个月后我们得到了实验结果。我的假设被证实,结果显示:当用基督教相关符号对身为教徒的实验对象进行刺激时,他们大脑中呈现兴奋状态的区域及其表现与品牌拥趸们接收到品牌符号信息时的状况极为相似。而那些消费者归属感并不强烈的品牌(比如肯德基或者英国石油)在实验对象大脑中所刺激到的区域范围要小得多,热烈程度也相应低得多。这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品牌与宗教间的关系研究所拿到的第一组确凿的证据。
同时,我们也对全球范围内14位宗教领袖进行访问,询问他们建立一种力量强大的宗教需要哪些因素。从他们的回答中,我们归纳出了以下这些要素:
第一个关键性因素是明确而清晰的愿景,这是构成宗教影响力最重要的基石,也是激励伟大行动与坚定归属感的源泉。那么,那些具有宗教般影响力的品牌拥有怎样的愿景呢?多年前,欧莱雅的品牌使命是——“我们只销售希望”。然后是苹果1982年的品牌愿景——“人类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他们应当用创造力来驾驭系统与结构,而不是沦为它们的附庸。”
其次,强烈的归属感。特百惠、哈雷·戴维森、乐高和苹果,这些品牌之间最大的共性是什么?它们都建立了一个充满归属感的集群。只要你开始成为乐高的拥趸,就会终身为之疯狂。我自己就是个乐高狂人,从12岁开始到现在,从未动摇。当你关注到乐高的品牌价值时,你一定会以为这家公司曾在营销预算上豪掷数十亿美元。事实并非如此。乐高在营销上的作为远远少于我们的想象,实际上,狂热的拥趸群体才是缔造乐高神话的关键。